6/10. 开篇两分多种的固定机位对准冰封江面上装扮尸体的昌浩,村长和老板娘走进时他一溜烟跑了,这其中流淌的悲伤情绪源自无法缝合想象与现实的桥梁纽带:村长老妈几番尝试阔从桥梁渡江,江上意味着想象中的归乡.
开篇两分多种的固定机位对准冰封江面上装扮尸体的昌浩,村长和老板娘走进时他一溜烟跑了,这其中流淌的悲伤情绪源自无法缝合想象与现实的桥梁纽带:村长老妈几番尝试阔从桥梁渡江,江上意味着想象中的归乡. 而现实中姐姐被脱北者强暴的昌浩守在江边用木棒击打准备上岸的脱北者,甚至对郑真送礼物的态度也发生粗暴转变.
而现实中姐姐被脱北者强暴的昌浩守在江边用木棒击打准备上岸的脱北者,甚至对郑真送礼物的态度也发生粗暴转变. 理想的祖国出现裂痕,是新闻里播出赞美金将军的讲话对应脱北者突发的性暴力,村民们食物被频繁来往的脱北者偷也动摇了孩子的同情心,愿意伸出援手的同时也带着防备手段和领政府奖励的告发心态,居住国与祖国的微妙情感关系,投注在藏身废墟里的踢球游戏和昌浩跃下房顶的死亡选择.
理想的祖国出现裂痕,是新闻里播出赞美金将军的讲话对应脱北者突发的性暴力,村民们食物被频繁来往的脱北者偷也动摇了孩子的同情心,愿意伸出援手的同时也带着防备手段和领政府奖励的告发心态,居住国与祖国的微妙情感关系,投注在藏身废墟里的踢球游戏和昌浩跃下房顶的死亡选择. 只拍摄无关事物的留白不能饱满人物的情感,显得空洞无意义,姐姐身体成为男性的泄欲工具和怀孕的圣母情结,以及昌浩结尾的殉道体现了观念的公式化.
只拍摄无关事物的留白不能饱满人物的情感,显得空洞无意义,姐姐身体成为男性的泄欲工具和怀孕的圣母情结,以及昌浩结尾的殉道体现了观念的公式化.
 佐临曾以“鸯蝴太轻”为由拒绝执导(《被我弄丢的你》原名为《被我弄丢的你》),轻,便是轻在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及批判稍欠力度.
佐临曾以“鸯蝴太轻”为由拒绝执导(《被我弄丢的你》原名为《被我弄丢的你》),轻,便是轻在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及批判稍欠力度. 40年代,进步文艺评论对喜剧依然抱持着相对暧昧、保守的态度,担心民众们在笑声中忘记了痛苦,疏泄了对现实的怨恨与不满.
40年代,进步文艺评论对喜剧依然抱持着相对暧昧、保守的态度,担心民众们在笑声中忘记了痛苦,疏泄了对现实的怨恨与不满. 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被我弄丢的你》当然是一个相当具有社会问题意识的代表性文本,它一点儿也不轻.
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被我弄丢的你》当然是一个相当具有社会问题意识的代表性文本,它一点儿也不轻. 虽然缺乏对复杂纷乱的现实情境的描摹,但彼时上海物价上涨、民不聊生等大量事实在细节的铺排中也可见一斑,且小人物们的思想和行动,都有当时社会现实的脉络可寻.
虽然缺乏对复杂纷乱的现实情境的描摹,但彼时上海物价上涨、民不聊生等大量事实在细节的铺排中也可见一斑,且小人物们的思想和行动,都有当时社会现实的脉络可寻. 石挥的戏剧式表演将五官及肢体开发到极限,李丽华也将媚俗而又矛盾的状态也演绎得细致入微,以至于在故事最后,当李丽华选择了“坐在自行车后座笑”而非“坐在宝马车上哭”时,竟是如此地合理且毋庸置疑.
石挥的戏剧式表演将五官及肢体开发到极限,李丽华也将媚俗而又矛盾的状态也演绎得细致入微,以至于在故事最后,当李丽华选择了“坐在自行车后座笑”而非“坐在宝马车上哭”时,竟是如此地合理且毋庸置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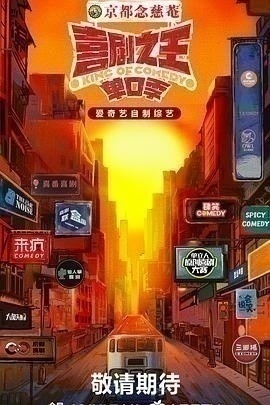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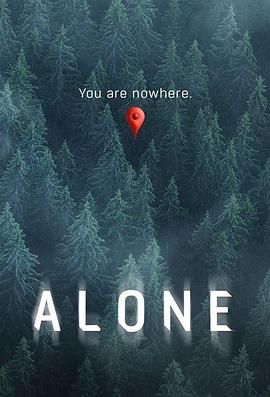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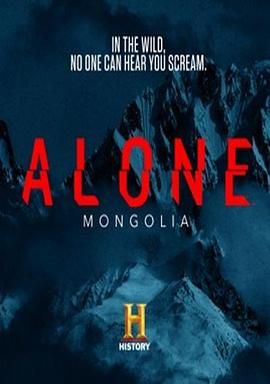



/107(16).png)